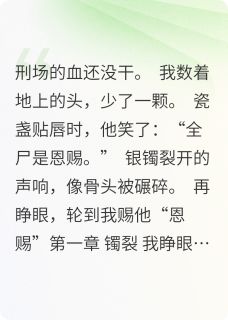最新小说《我重生后.比反派更疯批》,主角是李伟赵奎,由爱吃鱼的小姐姐创作。这本小说整体结构设计精巧,心理描写细腻到位,逻辑感强。故事情节跌宕起伏,让人痛快淋漓。非常值得推荐!内壁刻的“李伟”二字被血填满,像活了过来。“死也要烙住你。”我低笑,毒酒冲得眼前发黑。心跳声越来越慢,咚,咚——突然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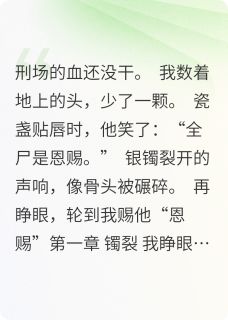
《我重生后.比反派更疯批》精选:
刑场的血还没干。我数着地上的头,少了一颗。瓷盏贴唇时,他笑了:“全尸是恩赐。
”银镯裂开的声响,像骨头被碾碎。再睁眼,轮到我赐他“恩赐”第一章镯裂我睁眼时,
天是红的。不是晚霞,是血。父兄的头滚到脚边,眼睛还圆睁着,像两盏被掐灭的灯。
刀光悬在头顶,却迟迟不落——他们舍不得给我痛快。李伟捏住我下巴,指尖冰凉,
带着龙涎香。那香气曾让我醉心,此刻却呕得我肝肠寸断。“元清,该谢我。”他笑,
左唇比右唇高半分的弧度,和眉心那颗痣一起,烙进我眼底,“赐你全尸。”瓷盏贴上唇,
苦液灌进来。鸩酒像团火,顺着喉咙烧进五脏六腑。我猛地咬舌,血混着毒酒涌出来,更苦。
疼让我清醒。腕间银镯在残阳里晃,亮得刺眼。是他送的,定情那日他说“生生世世,
锁你”。好啊,那就锁。我狠狠将镯子磕向青石。豁口划开掌心,血珠子争先恐后涌进镯内,
内壁刻的“李伟”二字被血填满,像活了过来。“死也要烙住你。”我低笑,
毒酒冲得眼前发黑。心跳声越来越慢,咚,咚——突然停了。……再睁眼,
铜镜里映出张干净的脸。没有血,没有泪,连头发都一丝不乱。刑台呢?父兄的头呢?
我抬手,银镯完好无损,银亮如新。假的?梦?我拔下金簪,狠狠刺向指尖。血珠滚出来,
滴进镯内。那血在镯里转了三圈,“啪”地撞上一道旧疤——和记忆里被镯沿划破的伤口,
分毫不差。我笑得喘不过气。时间被我撕回来了。舌尖的破口还在,毒酒的苦劲没散。
我低头吻了吻腕内侧,那里三个月后会烙上“三月”二字。李伟,你且等着。这回,
我亲手送你下地狱。夜风卷着沙子抽脸,生疼。我攥紧拳头——疼才好,
疼能让我记着自己还活着。三天。只剩三天。赵奎要用借据换虎符,
李伟要用虎符换我父兄的命。我转身走向夜色深处,腕间银镯轻轻晃了晃,像在提醒什么。
袖中匕首的寒意透过布料渗出来,我忽然想起李伟送镯时,
眸底一闪而过的、我当时没读懂的阴翳。那阴翳里,藏着的会不会不止是杀心?
第二章镜醒腕间银镯在夕阳里晃,亮得刺眼。是李伟送的。定情那日桃花纷飞,
他捏着镯子扣在我腕上,指尖的温度透过银器渗进来,说:“生生世世,锁你。”好啊,
那就锁。我猛地将镯子磕向刑台青石。豁口划开掌心的刹那,血珠子争先恐后涌进镯内,
像要钻进骨头缝里。内壁阴刻的“李伟”二字被血一填,竟像活了过来,
在残阳下泛着妖异的光。“死也要烙住你。”我低笑,喉间的鸩酒突然翻涌,
火烧火燎地窜向四肢百骸。又磕一次。镯沿划开的皮肉更深,血淌得更凶,
溅在他送的那枚玉扣上——那是他说要娶我时,聘礼里最贵重的一件。毒酒冲顶的瞬间,
我看见他站在刑台边,左唇比右唇高半分的笑里,藏着我从未读懂的冷。心跳声越来越慢,
咚,咚——突然停了。……再睁眼,铜镜里映出张干净的脸。没有血污,没有泪痕,
连鬓角的碎发都梳得整整齐齐。我抬手抚向脖颈,那里本该残留着被他掐过的红痕,
此刻却光滑一片。刑台呢?父兄滚落在脚边的头颅呢?腕间的银镯好端端扣着,银亮如新,
连半道划痕都没有。仿佛方才的血、火、撕心裂肺的疼,全是一场噩梦。我拔下鬓边金簪,
尖儿狠狠刺向指尖。血珠冒出来的瞬间,我把它滴进镯内。那血在镯心转了三圈,
“啪”地撞上一道浅痕——和记忆里被镯沿划破的伤口,位置分毫不差。铜镜里的我,
笑得比哭还难看。不是梦。我真的回来了。回到了一切都没发生的时候。指尖的刺痛还在,
舌尖的血腥味未散,可腕上的镯子却突然烫起来,像有团火在银器里烧。我低头去看,
镯心的“李伟”二字竟泛出极淡的红,像血渗进了银骨里。这时,
窗外传来丫鬟的声音:“**,李公子派人送了桃花酥来,说……说想邀您明日去城外踏青。
”我盯着铜镜里自己骤然变冷的眼,忽然发现,那镯子烫得越来越厉害,仿佛有什么东西,
正顺着血脉往骨头里钻。是他当年藏在镯子里的,除了“锁你”之外的东西吗?
第三章血证假的?梦?濒死幻觉?指尖的金簪被我攥得发烫,尖儿毫不犹豫对准指尖。
皮肉刺破的刹那,血珠滚出来,滚圆,像刑台上那颗没滚远的、父兄的头颅。
我把血滴进镯内。盯。那血在银器里转,转,转——像在绕着某个看不见的圈。
突然“啪”一声,撞在镯心一道浅痕上。和记忆里被镯沿划破的伤口,分毫不差。
连皮肉翻卷的弧度,都像是用同一把刀刻出来的。我笑了,笑得肺腑发疼,
眼泪混着笑滚下来。铜镜里的影子嘴角咧得极大,眼里却淌着血似的红,比哭还难看。
不是梦。时间真的被我撕回来了。舌尖的破口还在隐隐作痛,毒酒那股穿肠烂肚的苦劲,
像刻在味蕾上的烙印。我抬手抚过腕内侧,那里光滑一片,可我清楚记得,三个月后,
滚烫的烙铁会在这儿烫下“三月”二字——那是李伟给我这个“玩物”的编号。
“李伟……”我低念这两个字,牙齿咬得咯咯响,“这回,该我给你编号了。
”低头吻向腕间银镯,冰凉的银器突然泛起暖意,像有什么东西被血激活了。我猛地抬眼,
铜镜里映出镯心的“李伟”二字,竟泛着极淡的血色,像活了过来。这时,
窗外传来更夫打更的梆子声,三响。三更了。距离赵奎用借据换虎符,还有三天。
距离父兄惨死,还有三个月。我攥紧镯子站起来,指节泛白。铜镜里的人影眼神陡然变冷,
像淬了毒的刀。可就在转身的瞬间,我看见铜镜角落映出一抹极淡的红——不是我的血,
倒像是……从镯子里渗出来的。我猛地低头,镯子却又恢复了银亮的模样,
仿佛刚才的血色只是错觉。但指尖残留的暖意不会骗我。这镯子,
绝不止是定情信物那么简单。它到底藏着什么?是李伟故意埋下的眼线,
还是……能让我逆转更多事的钥匙?第四章赌命那里,三个月后,会烙上“三月”二字。
烙铁烧得通红时,李伟就坐在刑台边,看我疼得蜷缩,左唇比右唇高半分的笑里,淬着冰。
“李伟,你且等着。”我对着铜镜里的影子低语,指尖掐进掌心,“这回,
我亲手送你下地狱。”夜风卷着沙子抽脸,生疼。我攥紧拳头,
任由砂砾嵌进皮肉——疼才好,疼能让我清清楚楚记得,父兄滚落在地的头颅,
是怎样瞪着我的。三天。只剩三天。赵奎就要拿着管家儿子阿吉的借据,
来换父亲的虎符;而李伟,会用那枚虎符,来换我父兄的性命。不,是换他们的死法。
我裹紧斗篷,先去了“鸿运”赌坊。灯笼血红,把匾额上的“鸿运”二字照得像流脓的疮。
门口两个打手脖子粗得跟磨盘似的,见我是个女子,眼神里淌着轻佻。我把斗篷往下一扯,
露出半张脸——左眉骨下那道浅浅的疤,是幼时替父亲挡箭留下的,京中认得的人不少。
“叫你们东家。”我的声音裹着沙子,又冷又硬。门开了条缝,一股霉味混着烟味冲出来。
赌坊老板坐在太师椅上,脚尖晃着枚翡翠扳指,绿得像鬼火,足有人耳朵那么大。他笑,
露出颗金牙:“元大**也赌?玩多大?”我没答话,啪地把银票拍在桌上。五百两,
够寻常人家活十年。“五百两,换元福的儿子。”老板眯起眼,手指在银票上刮来刮去,
沙沙响,像在数上面的纹路:“晚了,赵大人已经定了价。”我猛地掀翻椅子,
拔下发间金簪,尖儿抵住他喉结。簪子上还沾着我的发油,此刻却凉得像冰。“那就换你命。
”金牙抖了抖,他喉结滚了滚,咽口唾沫:“后院水牢,自己去提。”水牢黑得像口井,
火把一晃,我看见阿吉泡在水里,右手包着破布,布条渗血。一根铁链穿过他琵琶骨,
锁骨处的皮肉磨得翻卷,白森森的骨头隐约可见。我蹲下去,声音轻得像叹息:“疼吗?
”他点头,眼泪鼻涕糊了一脸。我抽出靴筒里的匕首,寒光一闪。“咔。”一声脆响,
阿吉的尾指落在水里,溅起血珠。他惨叫,几乎晕厥。我捡起那截断指,塞进他嘴里,
逼他咬住。“再赌,就再断一根。”血腥味呛得他直呕,我却抓起他血淋淋的手,
按在赌契上。老板的脸青得像被水泡过的纸。“撕。”我盯着他,一字一顿。纸碎成雪,
飘落在地。我拖着阿吉往外走,背后传来老板咬牙的声音:“赵大人不会放过你!”我回头,
冲他笑了笑,那笑意却没到眼底:“让他来。”走出赌坊时,月光突然亮得刺眼。我低头,
看见腕间的银镯泛着冷光,镯心“李伟”二字的位置,不知何时多了道极细的红痕,
像血渗进去,又没完全干透。这镯子,在水牢里明明没沾血。我猛地攥紧手腕,
阿吉的惨叫还在耳边,可那道红痕却越来越清晰,像在提醒我什么。
难道……这镯子不只会带我回来,还能……看见些别的?第五章血契“后院水牢,
自己去提。”赌坊老板的声音像水里泡过的朽木,透着霉味。水牢黑得像口没底的井,
火把晃了三晃,我才看清泡在水里的阿吉——管家的小儿子,右手包着破布,布条浸得透红,
一根粗铁链从他琵琶骨穿过去,锁骨处磨得皮肉翻卷,白森森的骨头碴子看得人眼疼。
我蹲下去,火把的光映在他脸上,全是泪和鼻涕。“疼吗?”我的声音很轻,像怕惊着什么。
他拼命点头,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我抽出靴筒里的匕首,寒光在火把下闪了闪。“咔。
”一声脆响,阿吉的尾指掉进水里,溅起的血珠落在我手背上,烫得像火。
他发出杀猪般的惨叫,身子在水里剧烈挣扎,铁链勒得更深。我捡起那截断指,塞进他嘴里,
逼他咬住。“再赌,就再断一根。”血腥味混着水牢的腐味呛得他直呕,
我却抓过他血淋淋的手,按在赌契上。红手印像朵开败的花。老板的脸青得像块猪肝。“撕。
”我盯着他,一字一顿。纸碎成雪,飘在潮湿的空气里。我拖着阿吉往外走,
背后传来老板咬碎牙的声音:“赵大人不会放过你!”我回头,冲他笑了笑,
那笑意却淬着冰:“让他来。”夜深得像泼开的墨。回府时,管家正跪在影壁前,
头磕得咚咚响,青石板上已见了血。“**,救救犬子,赵奎的人明晚就要虎符!
”他声音嘶哑,像被砂纸磨过。我蹲下去,掐住他下巴,逼他抬头看我。
他眼里的恐惧像要溢出来。“想救?”我慢悠悠地说,“那就替我演一出。”他浑身哆嗦。
我从怀里掏出那枚锡箔假符,金粉在廊下灯笼的光里闪着冷光。“真虎符我爹贴身带,
你想办法换。”管家哭起来,老泪纵横:“将军睡觉都攥着钥匙——”我没等他说完,
抬手用匕首在掌心划了道口子。血珠滴进旁边的酒碗,在酒面上浮起细细的红丝,
像游动的蛇。“喝。”我把碗递到他面前。血腥味直冲鼻腔,他抖着双手捧起碗,
闭眼灌了下去,喉结滚动得像要卡住。我把匕首拍在他掌心,刃口贴着他的皮肉。
“若泄半个字——”我顿了顿,看着他的眼睛,“阿吉再断一指。”他瘫坐在地上,
像被抽走了骨头。我转身要走,腕间的银镯突然发烫,像有团火在里面烧。低头一看,
镯心“李伟”二字竟泛出暗红,像有血要从银器里渗出来。更诡异的是,那暗红的纹路里,
隐约映出个模糊的影子——像是个人跪在地上,背后插着箭,看服饰,竟有几分像我父亲。
这影子一闪就没了,快得像幻觉。我攥紧镯子,指尖冰凉。难道这镯子不只是能带人回来,
还能……预兆些什么?那影子,是父亲的结局,还是……别的什么第六章偷符“想救?
那就替我演一出。”管家浑身哆嗦,像秋风里的落叶。我从怀里掏出锡箔假符,
金粉在灯下闪着冷光,晃得他眼晕。“真虎符我爹贴身带,你想办法换。”他突然哭起来,
老泪糊了满脸:“将军睡觉都攥着钥匙——”我没耐心听他废话,
抬手用匕首在掌心划开一道口子。血珠坠进旁边的酒碗,在酒面上浮起红丝,像刚游过的蛇。
“喝。”我把碗递到他嘴边。血腥味混着酒香冲得人发晕,他抖着双手捧起碗,
闭眼灌了下去,喉结滚动得像要卡死。我把匕首拍在他掌心,刃口贴着他的皮肉。
“若泄半个字——”我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阿吉再断一指。”他“咚”地瘫坐在地,
像被抽走了骨头,眼神空洞得吓人。我转身披斗篷,翻窗时带起的风卷着夜露,
打在脸上冰凉。父亲在浴房,蒸汽缭绕得像团白雾,我贴着墙根滑进去,
指尖的金簪探进他束发的玉冠里。“咔哒”一声轻响,钥匙的齿痕拓在了早已备好的蜡块上。
一刻钟后,我蹲在耳房,锡箔在火上慢慢化开,像一汪流动的银。灌进模子,撒上金粉,
假符成型的瞬间,竟和真符有七八分像。我把真符塞进自己枕下,那里藏着最安全的暗袋。
再将假符放进原匣,锁扣“咔哒”合上,像关上了一道通往地狱的门。转身时,
腕间的银镯突然又烫起来。这次看得真切,镯心“李伟”二字的暗红里,
浮出串模糊的数字——像日期,又像时辰。更怪的是,数字旁边竟有个小小的虎符印记,
正一点点被血色吞噬。这镯子到底在示警什么?是说假符会被识破,
还是……真符藏在我这儿,本身就是危险?我攥紧枕头下的真符,冰凉的铜器硌得掌心生疼,
可镯子里的血色,却越来越浓了。第七章碎镯锁扣“咔哒”一声合上,像关上一道鬼门。
第二日,府里摆赏花宴。京中命妇来了大半,满头珠翠晃得人眼晕,脂粉香混着花香,
甜得发腻。我穿了件素白长衫,腕间银镯在衣料映衬下,亮得格外显眼。李伟来了。
他捧着顶凤冠,珍珠串垂落下来,晃悠着像一条吐信的毒蛇。“清清,戴上它,冲喜。
”他笑得温和,左唇比右唇高半分的弧度,和记忆里刑台上的模样重合。我后退半步,
抬手就将腕间银镯往旁边的剑架上撞去。“当啷!”一声脆响,银光四溅,
镯子碎成星子般的碎片。命妇们哗然,抽气声此起彼伏。我弯腰捡起最大一块碎片,
狠狠攥在掌心。锋利的边缘划破皮肉,血珠滚落在腕内侧,蜿蜒着晕染出两个字——断情。
我把碎片捧到李伟面前,掌心的血滴在他华美的锦袍上,像绽开的红梅。“还你。
”他脸色青白交加,手指死死攥着凤冠,指节泛白。太后派来的嬷嬷在旁边倒吸凉气,
眼神像要把我戳穿。流言像野火,借着手腕的风,一炷香就传遍了半个京城。
李伟当晚就进宫跪请退婚。我转身回房,掌心的血滴了一路,在青石板上连成线,
像给地狱引路的灯。夜里,丫鬟阿杏还没回。日头沉得只剩最后一丝光,我心里发慌,
像有蚂蚁在爬。割破指尖,把血涂在帕子上,唤来府里的老犬。它鼻子贴地嗅了嗅,
尾巴夹着,一路往府外跑,最终在后门巷子停住脚,对着一串马车辙狂吠。辙印很深,
泥里嵌着枚小小的王府徽记。我摸了摸腕间的伤口,那里还在隐隐作痛。这时,
袖中残存的银镯碎片突然发烫,像有火星溅在皮肤上。借着月光一看,
碎片边缘竟映出个模糊的影子——像是间地牢,角落里缩着个人,看身形,极像阿杏。
可那影子背后,还站着个穿玄色衣袍的人,手里拿着什么东西,正往阿杏嘴里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