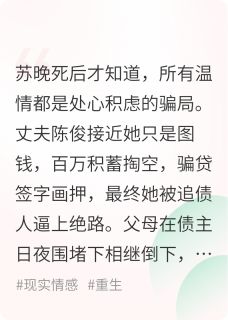《重生之送渣男进去》是一部极富想象力和奇幻色彩的短篇言情小说,由翱翔于天际的猪精心创作。故事中,苏晚陈俊置身于一个神秘的世界,展开了一段关于友谊、勇气和信任的冒险之旅。苏晚陈俊面对着各种魔法和怪物,通过智慧和勇敢战胜了困难,最终达到了目标。”苏晚按下了接听键,手机贴到耳边:“李哥,您说。”“哎,是这么回事!老哥我最近手头不是凑几个老兄弟想做点短平快的钢材批发……将带领读者进入一个神奇和令人着迷的奇幻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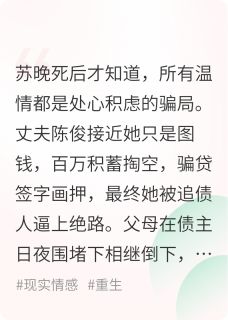
《重生之送渣男进去》精选:
苏晚死后才知道,所有温情都是处心积虑的骗局。丈夫陈俊接近她只是图钱,百万积蓄掏空,
骗贷签字画押,最终她被追债人逼上绝路。父母在债主日夜围堵下相继倒下,
弥留之际她眼中只有陈俊冰冷轻蔑的笑:“你真以为我爱你?”再次睁眼,
回到了灾难开始的三周前。她默默抽回曾紧握的手,眼神澄静冰冷。这一次,
她不用刀枪不用血,只需轻轻伸手把蠢货自己送进地狱。苏晚像是做了一场大梦。
梦里她已走完短暂一生。那结局真惨——逼仄出租屋,门窗被粗大铁链封死,
门板被泼满刺目红漆,像流不尽的血。死之前父母都不在了。
父亲扛不住高利贷追债凶神恶煞日夜围门吵闹,
脑溢血倒在家门口楼道再没起来;母亲精神崩溃,从七楼一跃而下。
最后只剩她独自蜷缩在门后水泥地上,肺里火烧火燎地疼,
气管像破风箱一样拉出一声声绝望的锐响。意识模糊那会儿,
门缝底下又被塞进一摞鲜红的催命符:法院传票,
限期执行令……债主们连最后一丝伪装都撕掉了。她记得自己是怎么被哄着签下那些字据的。
丈夫陈俊伏在她肩头,呼吸拂过她脖颈,温热温柔,说着那些掏心窝子的话。“晚晚,
咱们家底子薄,爸妈那边条件也一般,总得搏一把,是不是?
等我公司周转开就是几倍的利润,你签个字,我什么都给咱们挣回来!
”他的眼神像浸过温水,让人融化,“我这辈子最亏欠的就是让你跟着我吃苦。
”最可笑的是那句——“等这事成了,我就把公司转到你名下,晚晚,我只信你。”信?
苏晚死寂的眼盯着空无一物的墙壁。她信了。于是签字了,
家里银行卡一张张空了;她按陈俊手指点的位置签名了,
背上了一笔又一笔她从没见过的“共同债务”。死前最后见到陈俊,隔着被红漆泼洒的门缝。
债主的叫骂声、砸门声震天响,陈俊却不知用了什么法子硬挤出条缝看了进来。
视线对上她奄奄一息的样子,他眼中没有慌乱愧疚,只有种奇异的光亮,
不是急切心疼救她出去,而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冰冷的轻蔑。
那张曾在蜜糖里浸润过、在她耳边说过无数动人情话的嘴,动了动。隔着震耳欲聋的捶打,
苏晚从他的口型清晰地读出了最后那七个字。真以为我爱你?他笑了。
唇角往上勾起的弧度利得像手术刀划开了苏晚心脏,冰锥直**去旋转着捣碎最后一丝热气。
她那时已说不出话,只觉心口有什么东西猛地炸开,痛得她眼前彻底陷入永恒的墨黑。
窒息感和胸腔深处那炸裂般的剧痛清晰得如同发生在上一秒。
指尖仿佛还残留着地上冰冷的水泥触感,
耳边似乎还盘旋着门外地狱般的喧嚣和人濒死的嘶鸣……苏晚激灵灵打了个寒颤,
骤然睁开了眼。刺目的白炽灯光线劈进瞳孔,刺得她下意识地眯起眼。
窗外楼下隐隐传来的自行车**、路边摊贩模糊的叫卖……所有属于平凡人间的琐碎背景音,
带着一种难以置信的真实感,瞬间将她淹没。不是地狱的幽冷死寂。她下意识摸向胸口,
没有撕心裂肺的疼痛。她低头看自己的手,皮肤细腻光滑,
右手拇指指腹也没有被债主按着强行摁下印泥留下的那一点深红污迹。一切干净得可怕。
视线猛地定格——对面墙上,挂着一本崭新的日历。鲜红醒目的印刷体数字,
赫然标注着:2037年,4月7日。苏晚全身的血液,像是在这一刻彻底凝固、冰封。
心脏骤然停顿一瞬,随即疯了似的狂跳起来,带着一种要撞碎肋骨的力道,
在胸腔里擂动出震耳欲聋的声响。她几乎能听到那沉重、失速的回音在空洞的房间里撞击。
那一年。是那灾难开始前的三周!心脏在肋骨后面狂跳,撞得苏晚微微发抖。
她缓缓吸进一口气,带着初夏微尘的气息,再沉沉地呼出来。那动作极其细微,
仿佛怕惊扰了什么正在酝酿的黑暗风暴。目光转向身侧。床上微微塌陷下去,
一个人影挨得极近。阳光被碎花窗帘滤过,在他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是陈俊。
此刻他还睡着,浓密的睫毛在眼睑下方投下一小片恬静的阴影,
嘴角甚至还带着一点松弛下来的弧度,英俊无害。他的一只手越过窄窄的单人床界限,
覆在苏晚的手背上。指节修长,带着属于年轻男子的暖意。这温暖曾经像沼泽里的青藤,
温柔缠绕,拉着她一路陷进地狱深处。此时却像烧红的烙铁,烫得苏晚下意识猛地一抽。
睡梦中的陈俊似乎感觉到了动静。他发出一声模糊的低哼,浓密的眼睫颤动着,
眼看就要醒来。那覆在她手背上的手掌,似乎本能地要追着那份刚刚逃离的依偎,
手指微微曲起,试图抓住点什么。苏晚的眼神如同寒冬冻结的湖面,没有任何涟漪。
她静静收回手的动作像剥离一块肮脏的污泥,没有丝毫犹豫和留恋。指尖冰凉,
但动作平稳异常。她就那么看着陈俊慢慢睁开眼睛,那双曾哄得她交付一切的眸子里,
此刻只有被意外中断睡眠的惺忪和不设防的茫然。“唔……早……”陈俊含糊地开口,
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沙哑磁性,伸手习惯性地又要揽她的肩,
“再睡会儿……”手在半途却碰到了无形的墙壁。苏晚只是直勾勾地看着他,眼神平静,
甚至有些过分的空洞,像透过他的皮囊在看什么完全不同的东西。陈俊的动作顿住了。
阳光落在他伸出的手臂上,那悬空的手指显得有点僵硬。
他眼底那点惯有的温情像投入沸水里的薄冰,无声无息地化开了一层,
透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愕然。“怎么了?不舒服?”“没有。”苏晚的嗓子有点干涩,
像是很久没说过话。她避开陈俊再次试图靠近的手,撑着床铺坐了起来。
老旧床铺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呀”一声,格外刺耳。“做噩梦而已。”她补充了一句,
声音依旧平淡得听不出情绪。阳光照在她脸上,却仿佛照不进那双过于安静的眼睛深处。
“我去弄点早饭。”她一边说话一边掀开被子,赤脚踩上有些冰凉的地砖,
走向这个狭窄出租屋角落的简易灶台。步伐没有丝毫慌乱。只有自己知道,
胸腔里的那团冰在无声燃烧。火焰的温度,刺骨地冷。陈俊坐在床上,
看着苏晚清瘦的背影在狭窄的过道里忙碌。灶台点燃蓝色的火苗,冰冷的铁锅放了上去,
磕碰声在寂静的晨间格外清晰。不对劲。他试图重新拾掇起那副温存的面具,
动作却显得有些滞涩。这感觉很陌生。苏晚总是那样,像一缕没有脾气的风,
总是无声无息地依附着他,习惯性地靠近他手臂的温度。她的依赖,是他自信的基石。
可今天早上醒来,那只手的飞快抽离,以及她眼神里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空洞?
像是身体还在眼前,灵魂却隔着千山万水,冰凉地审视。“晚晚?”他又试着唤了一声,
声音放得更柔,带上了恰到好处的关切,“真没事?看你脸色不太好。
”这关心在过去屡试不爽。苏晚没有回头,背对着他,从橱柜里拿出两枚鸡蛋。
她的声音隔着煎锅油花的滋滋作响传来,依旧平稳无波:“都说没事了。梦都是假的。”假?
陈俊皱了皱眉,心底莫名窜起一丝细微的不安。他用力甩开这种荒谬的直觉,
身体往前倾了倾,脸上重新堆砌出那种令苏晚过去每每心软的期待笑容,
声音黏稠:“老婆……那个张总那边,真的不能再拖了。他那人……你也知道,规矩多,
合同上一点不满意就……”他刻意顿住,目光像有形的钩子,
黏在苏晚侧脸上:“我今天再去磨磨嘴皮子,但得拿出点诚意……你看,
咱们手头那个定期存款……”来了。苏晚搅动蛋液的手停顿了一瞬。
这就是第一次割肉的切口。
前世听到“张总规矩多”时那种生怕搅黄他生意的焦虑感没有出现。胸腔里不是愤怒,
不是悲哀,而是一种极度疲惫的冰冷。她看着铁锅里渐渐凝固的蛋液,
油温蒸腾的细小水珠模糊了视线。她缓缓转过身,目光落到陈俊脸上。
那双曾经让她沉醉的眼睛里,
此刻清清楚楚地盛满了被“事业”困扰的焦灼和某种势在必得的急切。那焦灼与急切之下,
没有一丝一毫对两人未来的真正担忧,只有攫取。“钱的事……”苏晚缓缓开口,声音不高,
却带着一种奇异的穿透力,让陈俊专注倾听的姿势更往前倾了些,“我昨晚想了想。
”陈俊眼神亮了一下,那种期待更浓了。他知道他的“晚晚”最心软,
最怕他皱眉、怕他“生意不顺”。“……再看看吧。”苏晚的下一句话轻飘飘的,
像一片羽毛落在他紧绷的神经上。嘎?陈俊脸上的表情一瞬间凝固了,
期待的笑容僵硬在嘴角。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再看看?”他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拔高了声音,
带着无法掩饰的惊讶和急切,“晚晚,那钱放银行是死的!投资进去才是活的!
咱们的启动资金……”“启动资金还没影子呢?”苏晚打断他,
语气平淡得像在陈述一个与她无关的事实。她转过身,用锅铲铲起凝固焦黄的蛋皮,
“张总那边没签约,谈再多启动资金也只是空壳子。急什么?
”鸡蛋在锅里发出“滋啦”的最后一声响动。苏晚熄了火。整个过程她背对着陈俊,
动作一丝不苟。窄小的空间里只剩下食物的香气和某种无声的对峙。
陈俊被噎得一时说不出话。这感觉太陌生了。她拿着盘子,转身放到靠墙的小折叠桌上。
“快洗漱。”她抬眼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声音没什么波澜,“我一会儿要上班。
”完全没接刚才那个话茬。陈俊感觉自己精心准备的一击软拳,结结实实打进了棉花里,不,
是打进了冰水里。他看着苏晚侧身走过,坐到了桌边的小凳上,拿起筷子。她垂着眼,
自顾自地开始吃,细嚼慢咽,仿佛刚才那场关于投资、关于两人“美好未来”的重要谈话,
被油锅里煎蛋的香气彻底盖了过去。那口憋着的气在陈俊胸口盘旋,不上不下,
卡得他极其难受。但他只能把那股邪火和疑虑死死压下去。行,再等等。
他盯着苏晚平静得可怕的侧脸,眼底深处闪过一丝阴沉的光。饭桌沉默得令人窒息。
苏晚坐在折叠桌一端,捧着一小碗温热的米粥,用调羹舀起,慢慢地送到嘴边。
每一口都嚼得缓慢而仔细,似乎在进行某种机械重复的仪式。窗外阳光正盛,透过窗户,
照亮空气里细小的微尘。陈俊就坐在桌子另一端。他面前也放着一碗粥,白瓷勺搁在碗边,
没动几口。他的目光粘在苏晚身上,带着一种不加掩饰的审视和烦躁。他几次想开口,
目光触及苏晚毫无波澜的脸,又硬生生憋了回去。这种静默比争吵更让人心烦。突然,
“嗡——嗡——”,一阵尖锐的震动打破了凝结的死寂。是苏晚放在桌上的手机。
陈俊几乎是立刻条件反射似的抬起了头,视线精准地钉在那振动的老式手机屏幕上。
苏晚的动作停顿了一下,放下调羹。她拿起手机,屏幕上赫然跳动着两个字——李哥。
她没开公放,但在这极度安静的斗室内,电话那头男人浑厚粗嘎的嗓音毫无保留地穿透过来,
透着江湖人士特有的熟稔和自来熟:“小苏啊!哈哈,没打扰你小两口吧?
”苏晚按下了接听键,手机贴到耳边:“李哥,您说。”“哎,是这么回事!
老哥我最近手头不是凑几个老兄弟想做点短平快的钢材批发么?就一水转手的生意!
几天就能回款!绝对的零风险!”电话那头声音洪亮,语气热络得能把冰块都捂化了,
“就差最后一笔‘过河’的本金啦!你看,上次跟你提过的那个想法,现在利息翻一番!
”苏晚的手握着手机,指关节微微发白,指尖因为用力而泛起青白。她的后背绷得笔直,
像拉满的弓弦。前世的场景排山倒海地挤压过来——被父母紧紧握住手签下的担保文件,
话那头仿佛还带着酒气的、油滑笑着的脸……他就是压垮父母、把催债人引上门的第一个鬼。
然而她的声音,透过电话传递过去,却只有一种被生活打磨久了之后的平和,
带着一点恰到好处的、属于平凡女人的疲惫:“李哥……这事,还得等两天。
”电话那头愣了一下:“诶?等两天?”“嗯,”苏晚的声音依旧平稳,
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难为情”,“家里亲戚那边催得也紧,
一点旧账……陈俊也周转呢,我刚凑给他那边了……实在不好意思啊李哥,
您也知道我们这小门小户的……”她说得含混又诚恳,点到了“亲戚旧账”,
又带上了“陈俊也周转”,几个小本生意人最能心照不宣、最能理解的“难处”字眼,
巧妙地把所有压力都包裹在了一层无奈的烟雾里。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李哥显然也没想到是这种回答。他打着哈哈:“哎呀,这样啊!理解理解!都不容易!
那我再找找别人!没事儿!回头再聊!”电话挂断了。忙音嘟嘟嘟地在静默的房间里回响,
一下下敲打着紧绷的空气。苏晚放下手机,指尖的僵硬缓缓松开。她没去看陈俊,
重新拿起调羹。就在她准备舀起粥时,一声压抑不住的“砰”从对面响起!
陈俊重重地把瓷碗顿在了桌上!碗底磕碰劣质塑料桌面的声音异常刺耳。粥水都溅了出来,
落在桌面上。苏晚抬头。陈俊脸上那种精心维持的温和早就被撕得粉碎,
被一种被愚弄后的惊愕、暴躁和深深的疑虑覆盖。因为睡眠不足和骤然动怒,
他的眼底有些发红。“你给他钱了?”他的声音绷得极紧,像一根随时要崩断的弦,
每一个字都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死死盯着苏晚的眼睛,
试图从里面找出哪怕一丝一毫说谎的心虚。亲戚?旧账?他妈的哪来的钱?!
苏迎着他的目光,那双眼睛像封冻的湖面,一丝涟漪也无:“谁?”“姓李的!
”陈俊猛地提高嗓门,手指几乎要戳到那部老旧的手机上,“你不是说亲戚催账?!
你把钱给谁了?!你哪有钱?!”“亲戚就是亲戚。”苏晚的声音平平地铺过去,波澜不惊,
“家里总有急用的时候。李哥问我借钱周转他生意,我没钱借。”她把粥勺重新浸回碗里,
搅动了一下,语气如同陈述再平常不过的事实:“他说的利息翻倍,
可咱们上次存的定期还有半个月才到期,我总不能把钱拿出来损失利息去借给他吧?
而且他倒腾钢材那行,我们不懂,别好心帮人最后坏了规矩。”她抬眼,
目光清凌凌地落在陈俊扭曲的脸上,“你觉得我该拿咱们的死期钱去借给他?
还是为了点高息去提前取款亏利息?”她语速不快,每一句话都像小锤子,
俊逻辑里最薄弱的环节上——钱在定期里不能动;高息伴随着高风险;生意不懂不能乱掺和。
一连串理直气壮的反问,直接把陈俊噎得脸色由红转青。他胸口剧烈起伏着,
那股被苏晚第一次顶撞、第一次失控的邪火“噌”地烧遍了全身,
偏偏又硬是找不到一个可以立刻发力的支点!她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这么清晰,
这么……噎人?!那种被棉花堵住、又被细针刺中的憋闷感攫住了他。
他几乎是从齿缝里挤出来:“行,苏晚,你行!”他猛地站起身,
带得凳子腿和地面刮出刺耳的长音,椅子差点翻倒。他看也没看桌上那几乎没动过的早饭,
一把抓起挂在门后挂钩上的西装外套,铁青着脸,大步走向门口。“砰——!
”门被重重摔上,震得整个门框似乎都在簌簌发抖。
狭窄的楼道里传来他怒冲冲、逐渐远去的脚步声。震耳欲聋的摔门声在墙壁间撞了一下,
然后重重地落回地面,激起一片细小的、悬在半空的浮尘。苏晚维持着坐在板凳上的姿势,
像一尊泥塑,一动不动。她甚至没去看那扇被他摔得几乎有些变形的门板。
瓷白的勺柄被她无意识地握在掌心,坚硬冰冷。过了大概有那么十几秒,或者更久一点,
勺柄上那坚硬的棱角因为被握得太紧,锐利地硌进了她的掌肉里。
她仿佛才被这微弱的痛感唤回神志。苏晚缓缓地、极其缓慢地低下头。视线落在自己掌心上。
那浅浅的压痕,很快就会消退。
不像前世死前的最后一眼掌心——被强行按在印泥盒里留下的,再也洗不掉的红。
她没有看那个被甩上的门。她低下头,把瓷勺里已经变得微温的最后一点白粥,
无声地送入口中。时间开始了。陈俊像是被那顿憋闷的早餐彻底点燃了。
苏晚的“再看看”像根针,扎在他膨胀的信心上。之后的几天,他沉默地吃完早饭就出门,
回来也拉着脸,或者干脆加班到很晚。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刻意制造的冷低压,
无声地向苏晚传递着“事业受阻我很烦躁都是因为你”的控诉。他不说话,
但用眼神和摔摔打打的小动作强调他的焦头烂额。“公司缺那笔钱,卡得难受。
”这是他端着碗闷闷不乐时冒出来的一句。“几个电话轮番催,人情不好做。
”这是他半夜抽烟回来,“嘭”地一声把钥匙扔在桌上时发出的喟叹。
这些曾让苏晚心惊胆战寝食难安的信号,这一次却像落进深潭的石子,
只在她冰封的心湖表面溅起一圈微小的涟漪,转瞬即无。她甚至开始有条不紊地整理物品,
从抽屉深处翻出一只磨损的旧挎包。这包用了好几年,背带接口处磨得发白,
拉链头也有些生涩。苏晚打开拉链,把手伸进最深的隔层摸索。
她的手指触碰到一块干燥、微微板结的老式肥皂头。她把它拿出来,放到一边。然后,
她摸到了几张叠得方方正正的、边角都磨出毛边的纸张,小心地拿出来,压在手掌下。
都是过去的“历史”。有她名字的,
最早几张和银行打交道的凭证——陈俊当初信誓旦旦说是公司“合理避税”,让她签的字。
还有一张是给李哥的担保文件草稿复印件,上面有她潦草的手写字迹。
这些文件在以前毫不起眼,可能比不上一张超市小票,签完就被她随手塞进了包里隔层深处,
早已遗忘。现在,它们在她手心微微发烫。像是冥冥中有根断掉的线头,她自己亲手抛下,
如今又被她的重生从深渊里带了回来。苏晚垂着眼,把它们一张一张地重新叠好,
叠成一个紧实的小方块,然后放进另一个她专门存放重要证件和卡片的旧钱包夹层里。
动作慢而稳定,像整理重要的考古文献。傍晚时,陈俊没像往常一样“加班”到深夜。
他回来得稍早,带着一身室外微凉的气息。进门那一刻,
他脸上残留着外面沾染的些许烦躁和疲惫,看见苏晚坐在床边整理衣物,
他眼神微微闪烁了一下,那点疲惫瞬间被一种惯常的、带着点讨好意味的光亮压了下去。
像变脸一样。“晚晚,”他走过来,挨着苏晚坐下,
手臂看似随意地搭在她身后的床头铁架上,姿态亲昵,把她半圈在自己可控的范围内。
他身上还残留着淡淡的烟草味,刻意放低放缓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刻意为之的无奈和期许。
“钱……真挤不出来了?”他侧着头,目光灼灼地看着她的侧脸。苏晚心里无声地冷笑。
前世,就是这样一步步踏进同一个坑里。她没有动,甚至没看他,
目光依旧落在手中正在叠的一件旧T恤上,
语气淡得像在谈论窗外的天气:“前两天不是说了?
李哥那边也急……”陈俊眼底飞快地掠过一丝不耐烦,快得几乎抓不住,
又被他用更深沉的“温柔”覆盖住:“那种临时拆借,就是周转几天,杯水车薪!
哪比得上我们公司的正路子?”他身体往前倾了倾,试图捕捉苏晚的目光,声音压得更低,
带着诱惑的磁性,“我仔细想了想,‘张总’那边的合同,有把握!只要前期周转过去,
后面就是一个接一个的项目!”他甚至用手指在空气里比划了一下,画了一个巨大的饼,
“到时候,那点定期利息算什么!”他的目光带着审视和一种隐晦的压力,
落在苏晚毫无波动的脸上。苏晚叠好T恤,放在床尾整齐的小衣服堆上。抬起头,
视线终于和他对上。那双眼睛清澈平静,没有任何被画饼诱惑的亮光,
只有一种纯粹的、探寻事实的直白。“有合同?”她问。简单三个字,
像一盆冷水浇在陈俊燃烧得正旺的**上。他脸上那种侃侃而谈、描绘宏伟蓝图的自信表情,
卡壳了一瞬。“合同……”他下意识地避开了苏晚过分澄澈的视线,喉结滑动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