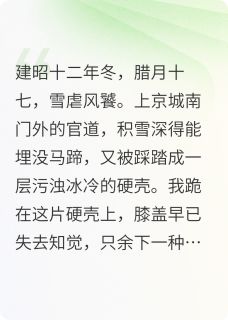梅骨寒小说剧情读起来真实有逻辑,人物形象很立体,非常耳目一新。小说精彩节选扫过跪迎的众人,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睥睨。那目光终于落到了我的身上,极其短暂的一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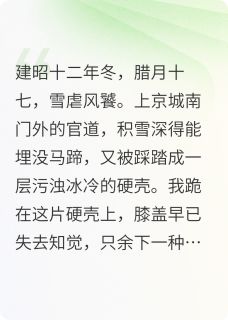
《梅骨寒》精选:
建昭十二年冬,腊月十七,雪虐风饕。上京城南门外的官道,积雪深得能埋没马蹄,
又被踩踏成一层污浊冰冷的硬壳。我跪在这片硬壳上,膝盖早已失去知觉,
只余下一种深沉的钝痛,沿着腿骨向上蔓延。身后是乌压压一片将军府的人,仆役婢女,
管事护卫,俱都垂着头,屏着呼吸,在这漫天风雪里凝固成沉默的石像。
冰冷的雪粒子被风卷着,狠狠抽打在脸上,又钻进脖颈里,激得人一阵阵发颤。“夫人,
您再往檐下避避风雪吧?”陪嫁的嬷嬷张氏不知第几次哑声哀求,
她粗糙冰冷的手试图将我搀扶起来,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您的身子骨……受不住的啊!
”我微微摇了摇头,动作牵扯到肩胛骨深处一阵沉闷的痛,那是前几日落下的寒气,
此刻在风雪里更如钝刀刮骨。目光固执地越过眼前攒动的人头,
投向官道尽头那片混沌的风雪迷蒙。那里,是凌墨渊归来的方向。“来了!将军回朝了!
”城门方向,不知是谁扯着嗓子喊了一声,那声音被风撕扯得变了调,
却瞬间点燃了整条官道。“是凌大将军!定北侯!咱们的大英雄回来了!”“快看!
将军怀里抱着的……天爷!那就是赫连部的昭阳公主吧?真跟画上的仙女儿似的!”“啧啧,
瞧那通身的气派,难怪将军……”汹涌的人潮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像沸腾的滚水,
瞬间淹没了风雪的呜咽。无数的声音交织着,
亢奋地议论着那个被凌墨渊护在怀里的、来自敌国赫连部的战利品——赫连昭阳。
她身上那件猩红如血的狐裘,即使在灰白的雪幕中也刺眼得灼目,像一道宣告胜利的烙印,
深深烫进我眼底。铁蹄踏破雪泥的声音由远及近,沉重而整齐,如同催命的战鼓,
一下下擂在我的心上。近了,更近了。我能看清为首那匹通体墨黑的神骏战马,
马背上端坐的,正是我的夫君,大梁的定北侯,凌墨渊。
玄铁重甲在灰暗的天光下泛着冷硬的幽光,肩头积了薄薄一层雪,更衬得那张轮廓分明的脸,
如同刀劈斧凿的寒玉。三年不见,他周身那股凛冽的杀伐之气愈发浓重,几乎凝成了实质,
让四周喧嚣的人群下意识地屏息后退,为他让开一条通路。他的目光锐利如鹰隼,
扫过跪迎的众人,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睥睨。那目光终于落到了我的身上,极其短暂的一瞬,
快得像错觉。没有温度,没有波澜,甚至没有一丝久别的意味,只有一种审视般的漠然,
仿佛在看路边一块碍眼的石头。下一瞬,他双腿猛地一夹马腹。“驾!”墨黑战马长嘶一声,
猛地加速前冲,碗口大的铁蹄重重踏下!“噗——”混着污泥和冰碴的雪沫,
被巨大的力量狠狠溅起,劈头盖脸地砸在我的脸上、脖颈上,甚至溅进了微张的口中。
冰冷、腥咸、带着泥土的腐味,瞬间封住了我的呼吸。刺骨的寒意沿着被污泥覆盖的皮肤,
瞬间钻入四肢百骸,冻得我浑身一僵。耳边是墨云骓粗重的鼻息和铁蹄踏雪的轰隆声,
还有风卷起赫连昭阳猩红狐裘一角时猎猎的声响。那抹耀眼的红,裹挟着冰冷的雪沫,
从我眼前疾掠而过,只留下一缕极淡的、属于陌生女子的幽香。人群的欢呼声浪更高了,
如同沸腾的海潮,将我这微不足道的狼狈彻底淹没。我僵在原地,
任由那些冰冷的污泥顺着脸颊缓缓滑落,在素色的衣襟上留下肮脏的印痕。“夫人!
”张嬷嬷带着哭腔扑过来,用她冻得发青的手,慌乱地、徒劳地替我擦拭脸上的污雪,
粗糙的指腹刮得脸颊生疼。她浑浊的老眼里满是惊惧和心疼,嘴唇哆嗦着,
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闭上眼,再睁开时,眼底只剩下死水般的沉寂。
喉咙里涌上一股熟悉的腥甜铁锈味,被我强行咽了下去,只在齿间留下一丝挥之不去的苦涩。
“回府。”声音哑得厉害,像被砂纸磨过。将军府,早已换了天地。府中张灯结彩,
红绸高悬,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一种刻意营造的、喧嚣浮华的喜气。仆役们脚步匆匆,
脸上堆着小心谨慎的笑容,往来穿梭,
将源源不断的珍馐美馔、华服锦缎送入西苑那座新辟出的“昭阳殿”。那殿宇据说耗费巨资,
引了活水温泉,四季如春,奢华程度远超主母所居的东苑“静芜院”。静芜院里,
却只有一种死寂的冷清。院中那几株我亲手栽下、精心侍弄了十年的老梅,虬枝盘曲,
在凛冽的寒风中抖擞着满树花苞,倔强地散发着清冷的幽香。这是这座冰冷府邸里,
唯一还带着点我苏晚气息的地方。张嬷嬷端着一碗黑漆漆的药汁进来,
浓郁的苦涩气味立刻在冷寂的屋子里弥漫开来。她将药碗放在我手边的小几上,
看着窗外那几株老梅,重重叹了口气:“夫人,您这又是何苦?将军他……唉,
那位主儿如今风头正盛,您何苦去碰她的霉头?那梅花……砍了也就砍了,
眼不见为净……”我正低头缝着一件小衣,是给府里管马的老王头刚出生的小孙子的。
指尖被冻得有些发僵,下针的动作却依旧平稳。闻言,只是指尖微微一顿,随即又穿针引线,
淡淡道:“花开花落,自有定数。这静芜院,也就剩这点念想了。”声音平静无波,
听不出情绪。话音未落,院门外骤然传来一阵喧哗。脚步声杂乱,还夹杂着几声尖利的呵斥。
“动作都麻利点!把这碍眼的东西统统砍了!一棵都不许留!没听见昭阳夫人的话吗?
这劳什子梅花的味儿,冲撞得夫人头疼!”一个尖细跋扈的女声响起,
是赫连昭阳从赫连部带来的贴身侍女,萨仁。我搁下手中的针线,走到窗边。
只见萨仁双手叉腰,趾高气扬地站在院门口指挥着。她身后跟着七八个粗壮的府兵,
手里提着明晃晃的斧头和锯子,正凶神恶煞地涌进院子,径直扑向那几株虬劲的老梅。
“住手!”张嬷嬷又惊又怒,踉跄着冲出去,张开双臂挡在一株最粗壮的梅树前,声音发抖,
“你们……你们好大的胆子!这是夫人的院子!这些梅树是夫人亲手栽的,
十年心血……”“滚开!老东西!”萨仁柳眉倒竖,上前一步,竟狠狠推了张嬷嬷一把。
老人猝不及防,哎哟一声摔倒在冰冷的雪地里。“嬷嬷!”我心头一紧,快步推门而出。
凛冽的寒风瞬间灌满了衣襟,冻得我打了个寒颤。目光扫过摔倒在地、狼狈不堪的老嬷嬷,
再看向那些手持利刃、虎视眈眈的府兵,最后落在萨仁那张写满得意与轻蔑的脸上。
“谁给你们的胆子,在我的院子里撒野?”我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沉沉的寒意,
压过了呼啸的风。萨仁被我的目光慑得微微一滞,随即又挺起胸膛,尖声道:“奉将军之命!
昭阳夫人闻不得这梅花的冲鼻气味,心口憋闷得慌!将军说了,
这静芜院里一切惹昭阳夫人不快的碍眼东西,统统清理干净!包括这几棵破树!
”她刻意加重了“将军之命”四个字,下巴抬得高高的。
将军之命……心口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剜了一下,瞬间空了一大块,只剩下冰冷的麻木。
我缓缓抬眼,望向西苑昭阳殿的方向。那里灯火通明,暖意融融,隐隐似有丝竹笑语传来。
呵。“砍吧。”我垂下眼睫,不再看任何人,声音轻得像一片羽毛落地,瞬间就被寒风卷走,
“都砍了吧。”萨仁得意地哼了一声,挥手示意府兵动手。“夫人!不能砍啊!
这是您的心血……”张嬷嬷挣扎着想爬起来阻止,被我轻轻按住了肩膀。“嬷嬷,
”我扶起她,替她拍掉身上的雪沫,声音平静得可怕,“树砍了,根还在。人活着,路就长。
”斧刃劈入老树躯干的沉闷声响,一声接一声,重重地砸在静芜院死寂的空气里,
也砸在我的心上。木屑纷飞,如同破碎的骨渣。虬结的枝干在利刃下痛苦地**、断裂,
砸在厚厚的积雪上,发出沉闷的噗噗声。那些含苞待放的花骨朵,来不及绽放,
便连同断枝一起,零落成泥,被肮脏的靴底践踏。空气里那股清冽孤绝的冷香,
迅速被浓重的、刺鼻的松木油脂味和木屑的腥气所取代。
那香气曾是我在这座冰冷牢笼里唯一的慰藉,如今,也彻底消散了。
我看着那些粗壮的树身轰然倒下,看着府兵们像拖拽尸体一样将它们拖出院门,
在雪地上留下凌乱而深重的拖痕,如同丑陋的伤疤。风卷起地上的残花和碎雪,打着旋儿,
扑在脸上,冰冷刺骨。静芜院,彻底空了。只剩下满地狼藉,和深入骨髓的、死一样的寂静。
张嬷嬷在我身边压抑地啜泣着,枯瘦的手紧紧抓着我的衣袖,像是抓住唯一的浮木。
我静静地站着,看着那片曾承载了我十年心血和最后一点念想的废墟,脸上没有泪,
只有一片荒芜的平静。指尖深深掐进掌心,留下几道月牙形的血痕,却感觉不到丝毫疼痛。
树砍了,根还在。人活着,路就长?呵。前路茫茫,哪里还有路?日子像结了冰的河水,
缓慢而滞重地向前流淌。静芜院彻底成了一座被遗忘的孤岛。炭火时断时续,
送来的饭菜也常常是冷的、馊的。下人们远远避开,生怕沾上这里的晦气。
只有张嬷嬷拖着病体,还在艰难地支撑着,为我煎药,替我挡去一些明里暗里的刁难。
她的咳嗽声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撕心裂肺,每一声都敲打在我早已麻木的心上,
提醒着我这无望囚笼的冰冷。府里关于西苑昭阳殿的喧嚣和奢靡,却像长了翅膀的风,
无孔不入地钻进这座孤岛。赫连昭阳染了风寒,凌墨渊彻夜守在榻前,
宫里的太医流水般地被请来,名贵的药材堆满了库房。赫连昭阳想吃南疆的鲜果,
八百里加急的驿马便踏着风雪奔驰。赫连昭阳嫌府里的绣娘手艺粗陋,
凌墨渊便重金从江南聘了最好的绣娘入府。赫连昭阳……赫连昭阳……这个名字,
连同它代表的荣宠与骄纵,成了悬在将军府每个人头上的金铃,时时刻刻叮当作响。
而我苏晚,连同这座破败的静芜院,不过是角落里无人问津的尘埃。腊月廿八,小年夜。
府里更是热闹到了极点。西苑昭阳殿灯火璀璨,丝竹管弦之声彻夜不息,
欢声笑语隔着重重院落和高墙,依旧隐隐传来,像无数细小的针,扎在耳膜上。静芜院里,
只有一盏昏黄的油灯,映着我和张嬷嬷相对枯坐的影子。桌上是一碗早已冰冷的薄粥,
几块干硬的点心。炭盆里只有零星几点暗红的火星,挣扎着散发最后一丝微弱的暖意。
张嬷嬷强撑着精神,想给我讲些旧年苏府的趣事,刚开了个头,便被一阵剧烈的咳嗽打断。
她佝偻着背,咳得撕心裂肺,枯瘦的手紧紧捂着嘴,指缝间渗出暗红的血丝。“嬷嬷!
”我心头剧震,慌忙起身扶住她摇摇欲坠的身体,触手一片滚烫,“你发热了!
”“没……没事,老毛病了……咳咳……”她喘着粗气,脸色灰败,
眼神却依旧执拗地看着我,充满了担忧,
“夫人……您……您要好好的……苏家……就剩您了……”“别说话!”我声音发颤,
强行压下喉头的哽咽,“我去求药!
”“不……不要去……别去求他们……”张嬷嬷死死抓住我的手腕,
枯瘦的手指却没什么力气,眼神里满是哀求,
“老奴……撑得住……”看着她眼中深切的恐惧和哀求,我如坠冰窟。求?向谁求?
去求那个此刻正拥着新欢、在西苑彻夜笙歌的凌墨渊?
还是去求那个视我为眼中钉的赫连昭阳?那无异于自取其辱,甚至可能加速嬷嬷的死亡。
一股巨大的、冰冷的绝望攫住了我。我眼睁睁看着这世上最后一点真心待我的温暖,
在我怀中一点点微弱下去,却无能为力。这一夜,静芜院的黑暗,浓稠得化不开。雪,
断断续续又下了几日。上元节刚过,一场倒春寒来势汹汹,将整个上京重新裹入酷寒之中。
这天午后,静芜院那扇几乎无人踏足的门,被猛地撞开了。
凌墨渊高大的身影裹挟着一身凛冽的寒气与暴怒,像一尊煞神般闯了进来。
他玄色的锦袍下摆溅满了污泥,显然是疾驰而来。那张素来冷峻的脸上,
此刻布满了骇人的戾气,双目赤红,如同被激怒的凶兽,死死地锁定了坐在窗边榻上的我。
他身后跟着几个同样面带煞气的亲兵,还有哭得梨花带雨、几乎站立不稳的赫连昭阳,
她被萨仁和另一个侍女搀扶着,脸色苍白如纸,手紧紧捂着小腹,
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怨毒和惊惧。“苏晚!”凌墨渊的声音如同炸雷,裹挟着滔天的怒火,
瞬间震碎了屋内的死寂,“你这个毒妇!”我缓缓抬起头,
放下手中那本看了许久也未曾翻过一页的书卷。指尖冰凉,心头却一片诡异的平静。该来的,
终究还是来了。“将军这是何意?”我迎上他那双燃烧着怒焰的眼睛,声音平静无波。
“何意?”凌墨渊怒极反笑,那笑声却比外面的寒风更刺骨。
他猛地从身后亲兵手中夺过一个东西,狠狠砸在我的脚下!那是一只小巧精致的鎏金手炉,
正是我冬日里常捧在怀中的旧物。此刻炉盖翻落,里面残留的炭灰撒了一地。
炉壁上沾着些暗红色的、早已凝固的血迹,触目惊心。“你自己看看!这是什么!
”凌墨渊的声音因暴怒而嘶哑,每一个字都淬着冰渣,“昭阳小产了!
太医在她常用的安胎药渣里,验出了极阴寒的‘血凝霜’!
而这毒——就是下在你这个手炉的炭灰里!每次她来你这破院子,
你都假惺惺地让她抱着暖手!好深的心机!好毒的手段!”他的指控如同淬毒的利箭,
铺天盖地射来。赫连昭阳适时地发出一声凄楚虚弱的呜咽,
身体软软地往下坠:“将军……妾身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好痛……”凌墨渊闻声,